同庚、同乡、同届、同道、同榜、同行……偌大个中国书法界,数来数去,可以用这么多“同”来相称的,大概也只有贤伦兄了。我们是同龄人,有着类似的学书经历,我熟悉他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观察他的学书经历,也给了我回顾上海和我们这一代爱好写字的人们艺术成长历程的一个机会。
污泥泵品牌
贤伦兄和我开始在上海学书法时,已是“文革”的后半期,政治空气逐渐宽松,上海的遗老遗少们,在临池自娱之余,有了私下授徒的机会。私授的学生多由亲友介绍,或是邻居的孩子。在那个年代,前辈们传授书法并不收费,见到好学的孩子们,总是爱护有加,而孩子们的日常请教,也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和实现自己的文化价值的一个途径。那时候的学习条件远不及今天,缺乏好的范本,很多字帖印刷质量不佳。但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没有什么功利心。贤伦兄在上海师从张大千弟子徐伯清先生。徐先生擅长小楷,贤伦兄曾说,徐先生对学生采取的是魔鬼训练营式的教学,他曾因在同门中率先临毕五十万字的小楷而得到老师的表扬。
贤伦兄在首届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中的获奖作品是隶书。由于获奖作品集印刷质量不佳,我们只能从中窥见贤伦兄获奖作品的大致面貌。好在他保存了两张同时期的隶书作品,与获奖作品风格一致,可以了解那时他的隶书的一些特征。作于1981年的《春眠不觉晓》条幅,汉碑加上一些汉简波磔的笔意,结字比较质直。下一年的《室雅、花香》对句,点画虽更为浑厚,路数却完全相同。虽说人们学书通常都会临习古代碑帖,但这种隶书,却明显带有上海时风。
不甘守成和求变意识,大概萌生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作于1997年的隶书对联《碧野、黄河》,不似当年获奖作品时那样含蓄规整,汉碑质直的意味褪去,用笔的速度明显加快,一如汉简。作于1999年的隶书《陈洪绶西湖垂柳图》,可以视为贤伦兄的变法前奏。这一作品虽然在基本型态和体势上还可归入隶书,但混杂了楷书、篆书、行书的因素。字的大小高矮、结体的欹侧、用笔的轻重,变化差别都很大。汉简中本来就有不少草写,这样的处理,写得生动,但基本还脱离不了一个“巧”字。
在和这件作品同时发表的《我是这样写字的》短文中,贤伦兄在提到了当代隶书取法战国、秦汉、三国简牍帛书的风气后,这样写道:“简帛书是个大金矿,但入口处难找到。看看都是闪光的,未必就是真金。这是读识的困难。从罗振玉、王国维编著的《流沙坠简》到新近的考古资料,在我案头也堆积如山了,可我又何曾识得它们?似曾相识已经造成视觉麻痹,用自己的眼睛来读识是件艰难卓绝的事。残酷的事实是,这么多的淘金者聚集在竹木简的矿藏浅层,模模糊糊地、浅俗地、人云亦云地、互相鼓舞地写着写着。我就是其中一员。”今天看来,这段难得的夫子自道,既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彷徨,也反映出他面对喧嚣的书坛时的冷静和清醒。
贤伦兄2002年以后的隶书,取早期隶书的圆浑厚重,避免了将轻盈一路的汉简放大时容易出现的单薄。如书于2003年的榜书《气腾八荒》,第一、第三字仅二三笔,结构简单,但点画圆浑壮硕,令人想起清人伊秉绶。而伊书取自《衡方碑》,虽气势宏大,但由于用笔缓慢,缺少了书写性,装饰意味浓重,有时流于呆板。贤伦兄的榜书,则汲取了晚期汉简迅捷的用笔,用来避免硕壮的点画走向滞呆。
静脉胰岛素用法与用量计算泵
书于差不多同一时期的对联《秦世、汉宫》,上下联起始于“秦”“汉”二字,可见,秦汉遗迹所呈现的精神世界令贤伦兄梦寐以求。此联中的“秦”“书”“汉”“新”等字,取秦简和马王堆帛书结字方法,形体偏高;“宫”与“字”的外框粗重,保留了成熟汉碑字形方正的特征;高矮相间,生动活泼。简牍多为日常书写的墨迹小字,书写性本来就强。贤伦兄在汲取了它们的精髓后,用厚重的用笔来书写榜书和对联,既有恢弘的气象,又不时透露出生动活泼的意趣;既高古,又富有现代气息。
仪表儒雅、谈吐温和的他,始终怀抱着求新思变的渴望,追寻秦汉梦想的脚步,并未在以简帛书带动的变法获得巨大成功时就此停住。2008年后,贤伦兄开启了另一项尝试:温故知新,以汉碑摩崖之宏大气象,创作巨幅书法。这一创作的冲动,既是艺术追求内在逻辑的展开,也有外部环境的催化。
吃什么肌肉会泵感
贤伦兄曾在回答一位记者关于自己的隶书受到汉碑和秦汉简牍的双重影响时,对两者的关系有着言简意赅的精辟论述,他说:“如说两种影响的区别,汉代碑刻和摩崖的影响是根本性的,秦汉简牍的影响则是附丽性的。”
上引这段文字的最后一句值得玩味,贤伦兄虽以“根本”与“附丽”作为区分,但实质上两者又是相互成全,这就譬如“文”与“质”,兼之者方可“文质彬彬”,缺一不可。这段采访也说明,不断地游走于汉碑和秦汉简帛之间,左右逢源,应是一种常态。重返汉碑摩崖,寻找探索的新支点,是他个人艺术追求内在逻辑展开的自然结果。
研究当代书法的人们都注意到了,20世纪中国书法的重要变化之一,便是从书斋走向展厅。近30年来中国经济腾飞,物质生活改善,新建的博物馆、美术馆如雨后春笋。当下美术机构的展示条件,吸引着书法家创作巨幅作品以取得震撼性的视觉效果。这是促使贤伦兄重返汉碑和摩崖的外部缘由。
贤伦兄2008年在宁波美术馆、2014年在中国美术馆、2016年在鲁迅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的个展中,都有巨幅作品。此次在上海中华文化宫的展览也不例外,有高5米、宽20米的巨幅作品《急就章》。如果比较这十二年来的巨幅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书于2019年的《急就章》,越来越多地掺入了汉碑和摩崖的形式因素。作为书写,怎样才能在平整的宣纸上表现出汉碑和摩崖拓片上那种混沌苍茫的气势呢?和书写简帛时的轻快不同,贤伦兄在书写《急就章》时,更多地使用中锋,点画显得圆浑,但略显迟涩的行笔,增加纸笔的摩擦力,留下些许“残破”的痕迹。在结字方面,除了少数一些字借取了早期简牍帛书的结构外,大多取汉碑的方正宽博。章法上,不似许多汉碑因刊刻时有界格而排列整饬,更像在摩崖之上信笔抒发,大小错落,左右穿插,不拘一格,整体气势也因之更为自由、开张、恢宏。
此次贤伦兄的个展名曰“大块文章”,与其气势磅礴的书法,可谓名副其实。举办展览的城市,则是我们共同的成长地——上海,一本更大的书。明年将是首届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40周年。那次竞赛上海大学生的总体出色表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世纪30年代到上世纪70年代上海积淀的深厚书法底蕴。当时在上海以外的大学获得一等奖的共有4位:贤伦兄、郑达。郑达长我一岁,擅长隶书,他参赛的作品在汉碑中揉入了金农的笔法,古朴灵动,作为获奖的代表性作品刊登在创刊不久的《中国书法》杂志上。毕业后,他到美国攻读英美文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一直在波士顿的一所大学教书,基本放弃了书法的追求。宝麟兄是以研究生的身份参赛,他那手精彩的米字,在获奖者中最受瞩目。40年来,他每日临的依然是米芾、苏轼、黄庭坚,从无“创新”的焦虑。他撰写的专著、论文和题跋,都与北宋人的生活与艺术相关。滋育他的书法的是完整的古典知识体系,他悠游其中,安身立命。宝麟兄和贤伦兄,代表着对书法的两种不同态度:一个是传承的典型,一个是创新的范例,两者皆可名于当代,传之后世。而我,则借着贤伦兄在上海举办书法展的机会,写下自己观察那些仍在砥砺前行的同代人的感想。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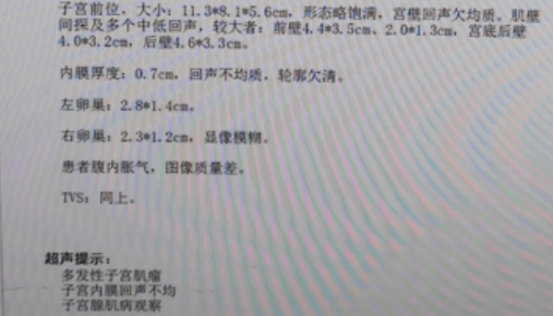

 排行榜
排行榜 最新看点
最新看点 编辑推荐
编辑推荐




